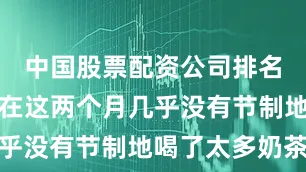「浦安修同志,彭德怀同志的平反决定下来了!」
年轻干部高兴地递过文件。
「平反...他等了十七年的平反..」
「这是好事啊!彭老总可以瞑目了!」
瞑目?这两个字像刀子一样扎进她心里。1962年那个秋天,她亲手吃下了分梨,1974年他病危时,她拒绝见最后一面。
良久,这位58岁的老人抬起头,颤声问出一句话。
让这位年轻干部愣住了,办公室里死一般的寂静。

01
1959年的夏天,对于41岁的浦安修来说,是人生的分水岭。
「浦书记,听说了吗?庐山会议的事...」同事欲言又止。
浦安修抬起头,心里咯噔一下。
「我相信组织,相信老彭。」她平静地说,继续低头批改作业。
可是纸上的字却模糊了。
结婚二十一年来,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了。

那是个心直口快的人,从来不会拐弯抹角。
在战场上,他敢于直面千军万马;在会议上,他也敢于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。
几天后,消息正式传来:彭德怀被撤销了国防部长职务,被定性为「反党集团」的首要人物。
那个晚上,浦安修独自坐在宿舍里,望着墙上丈夫的照片发呆。
照片上的彭德怀穿着军装,目光坚毅。
她喃喃自语:「二十多年了,我没听你讲过一句对党不满的话,怎么会成了反党集团的头目?」
周末,她去了吴家花园。
那是组织上新安排给彭德怀的住处,说是住处,其实就是几间简陋的平房,连基本的家具都没有。
彭德怀正在院子里锄地。看到妻子来了,他放下锄头,擦了擦额头的汗水:「来了?」
「嗯。」浦安修走过去,想说什么,却不知从何说起。
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」彭德怀坐在石凳上,「我没有反党,我只是说了一些实话。相信历史会证明一切的。」
浦安修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:「我相信你。可是...可是他们都说...」
「别人说什么不重要。」彭德怀握住妻子的手,「重要的是,你相信我吗?」
「我当然相信!可是老彭,现在的形势...」
就在这时,院门外传来了脚步声。
是北师大的几个同事来了。看到浦安修在这里,他们的表情有些尴尬。
「浦书记,您也在啊。」领头的干部清了清嗓子,「我们是来...来看看彭老总的。」
送走了客人,彭德怀叹了口气:「安修,以后你来看我,恐怕会给你带来麻烦。」
「什么麻烦?你是我丈夫,我来看你天经地义!」
彭德怀苦笑:「现在我是『反党分子』,你是北师大的党委副书记...」
话没说完,但两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
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政治立场高于一切,包括夫妻感情。
回到学校,浦安修发现自己的处境确实变了。
走在校园里,原本热情打招呼的师生们开始躲避她的目光。
开会时,原本坐在她旁边的同事会找借口换位置。
食堂打饭,服务员看她的眼神都带着异样。
「浦书记,」一天,组织部的领导找到她,「有个事想跟您谈谈。」
浦安修知道,该来的终于来了。
「关于您爱人的问题,组织上很重视。作为党的干部,您应该站稳立场,分清是非...」
这样的谈话,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。
每一次,都像一把钝刀在割她的心。
她能说什么呢?说丈夫是冤枉的?那就是对抗组织。
说丈夫真的反党?那违背了她的良心。
二十一年的革命伴侣,难道真的要在政治风浪中分道扬镳吗?
她想起1938年在延安,经陈赓介绍,她第一次见到彭德怀的情景。
那个在战场上威风凛凛的将军,面对她时却有些腼腆。他们一起度过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...如今,和平年代反而要面临最严峻的考验。
窗外,北京的夜空繁星点点。浦安修知道,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。她和彭德怀的命运,就像风中的落叶,不知会飘向何方。
02
日子一天天过去,压力像一座大山,越来越沉重地压在浦安修身上。
1960年春天,北师大要进行新一届党委选举。
按理说,作为党委副书记的浦安修,连任应该没有问题。
她在学校工作多年,无论是教学还是管理,都得到师生的认可。
可是,当选举结果公布时,名单上没有她的名字。
「浦书记,这个结果...」支部的老同志私下找到她,话说了一半就说不下去了。
浦安修淡淡一笑:「我理解。」
食堂里,她端着饭盘找位置坐下,原本热闹的餐桌突然安静了。几个年轻教师匆匆吃完,找借口离开。剩下的人也是埋头吃饭,不敢看她一眼。
「浦老师,您慢慢吃,我还有课...」 「我也是,下午有个会议...」
很快,偌大的餐桌只剩下她一个人。
有一次,她在走廊里碰到多年的老朋友,对方看到她,竟然转身就走。
浦安修追上去:「老王,你躲什么?」
老王尴尬地停下脚步:「没...没躲。浦书记,我真有急事。」
「我们认识二十年了,你有什么话直说吧。」
老王左右看看,压低声音:
「浦书记,不是我要躲您。可是...可是现在这个形势,跟您走得太近,对谁都不好。您...您自己保重吧。」
说完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浦安修站在空荡荡的走廊里,心里一阵酸楚。
在那个年代,自保是人的本能。
组织上的谈话也越来越频繁,说话越来越直接。
「浦安修同志,」党委书记找她谈话,表情严肃,「关于彭德怀的问题,组织上希望你能有个明确的态度。」
「我的态度一直很明确,我相信党,相信组织。」
「那你对彭德怀的错误怎么看?」
浦安修沉默了。
她能说什么?说彭德怀没错?那就是对抗组织。说他错了?那违背了她的良心。
「作为他的爱人,你最了解他。组织需要你提供一些情况...」
「书记,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。老彭他...他就是个直性子,说话不会拐弯。」
「浦安修同志!」书记的语气严厉起来,「你要认清形势!彭德怀是反党集团的头目,你作为党员,应该站在党的立场上!」
他们要她「揭发」彭德怀,要她「划清界限」,要她「站稳立场」。
每次谈话后,浦安修都觉得自己像被掏空了一样。
她开始害怕去学校,害怕面对那些审视的目光,害怕那些没完没了的谈话。
周末回吴家花园的次数,也越来越少了。
不是她不想去,而是每次相见,都变成了一种煎熬。
两个人坐在那里,往日的温馨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令人窒息的沉默。
「最近学校怎么样?」彭德怀会问。「还好。」她简单回答。「他们...没为难你吧?」 「没有。」
谎言。当然是谎言。可她不想让已经承受巨大压力的丈夫再为她担心。
她想起战争年代,他们一起出生入死。想起新婚时,彭德怀对她说:「我爱你的家乡,愿与你同归。」

可是现在,那个说要与她同归的人,成了「反党分子」。而她,必须在丈夫和党之间做出选择。
夜深了,浦安修躺在床上,泪水打湿了枕头。窗外的风呼呼作响,就像她内心的挣扎,找不到出路。
03
三年了,整整三年的煎熬。她已经快要撑不住了。
精神的折磨让她日渐憔悴。照镜子时,她几乎认不出自己——才44岁的人,看上去像是老了十岁。
终于,在一个失眠的夜晚,她做出了一个让自己悔恨终生的决定。
她要写离婚申请。
申请被逐级上报。先到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那里,又转到杨尚昆手中,最后送到了邓小平的案头。
邓小平看了看,在上面批了八个字:「这是家务事,我们不管。」
申请被退了回来。组织上不同意,但也不反对。
这个烫手的山芋,谁都不想接。
浦安修进退两难。既然已经提出来了,总要有个了结。
她不敢自己去面对彭德怀,只好请侄女彭梅魁代为转达。
彭梅魁后来回忆,当她把这个消息告诉彭德怀时,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,久久地坐在那里,一言不发。
过了很久,他才开口:「我理解她。这三年,她承受的压力太大了。离就离吧,这也是迫不得已,是政治需要。」
1962年10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,天气已经很凉了。
浦安修在彭梅魁的陪同下,来到吴家花园。
推开门,看到屋里还有一个人——彭德怀的老朋友杨献珍。
气氛很压抑。谁都知道今天来是干什么的。
彭德怀起身,到厨房拿出一个大梨。
他坐下来,拿起水果刀,仔细地削皮。
削完皮,彭德怀把梨放在盘子里,举起刀,稳稳地切下去。咔嚓一声,梨被切成均匀的两半。
他把盘子推到浦安修面前。
「吃吧。」他的声音很平静。
浦安修的眼泪刷地流下来。
「你这是干什么?彭老弟!」杨献珍不高兴了。
彭德怀看着浦安修:「我同意离婚,但我不吃梨。因为在我心里,我是不愿意分手的。」
他停顿了一下,继续说:
「安修,你要是坚信我彭德怀是个无辜受害者,你就不要吃梨。如果你有一丁点儿怀疑我是个反字号人物,就请痛痛快快地吃掉你的那半个梨。从此,我们一刀两断。」
这话说得太重了。浦安修哭得更厉害了。
她当然相信彭德怀是无辜的!
这三年来,她从没怀疑过这一点。可是...可是她真的撑不下去了。
「安修,不要吃梨!」杨献珍急了。
浦安修看看杨献珍,又看看彭德怀。彭德怀正定定地看着她,目光里有期待,有失望,更多的是理解。
她颤抖着伸出手,拿起了那半个梨。
时间仿佛凝固了。所有人都盯着她的手。
她把梨送到嘴边,咬了一口。梨很甜,可她觉得苦。苦到心里去了。
她一口一口地吃着,泪水和梨汁混在一起。
啪!
彭德怀突然站起来,抓起剩下的那半个梨,狠狠地摔在地上。
梨摔得粉碎,汁水四溅。
「老彭...」浦安修哽咽着。
彭德怀转过身,背对着她:「你走吧。以后保重。」
「老彭,我对不起你...」
彭德怀没有回头,大步走进了里屋。
浦安修瘫坐在椅子上,放声大哭。彭梅魁和杨献珍面面相觑,不知如何是好。
哭了很久,浦安修才站起来,踉踉跄跄地往外走。
走到门口,她回头看了一眼。这个简陋的小院,这个她来过无数次的地方,从此将与她无关了。
那个为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的元帅,那个陪伴她二十四年的丈夫,从此将独自面对人生的风雨。
而她,将带着这份永远无法弥补的愧疚,度过余生。
回到学校,浦安修病倒了。高烧不退,说胡话,在梦里一遍遍地喊:「老彭,我错了...」
可是,覆水难收。有些事,一旦做了,就再也无法挽回。
04
分梨之后,浦安修以为自己会轻松一些。可事实证明,她错了。
虽然没有正式办理离婚手续,但在政治上,她已经不再是「彭德怀的老婆」。可讽刺的是,这个身份的改变,并没有给她带来解脱。
1966年,山雨欲来。
1967年,风暴终于降临。
那是8月的一天,北师大召开批斗大会。浦安修本以为自己已经「划清界限」,不会再受牵连。
可当她被押上台时,才明白自己有多天真。
「浦安修!你以为写个离婚申请就能蒙混过关吗?」
「你跟反党分子彭德怀生活了二十多年,你敢说你什么都不知道?」
更让她震惊的是,彭德怀也被押来了。
当她看到那个曾经威风凛凛的元帅,如今白发苍苍、步履蹒跚地走上台时,她的心都碎了。
批斗会上,造反派对他们轮番攻击。浦安修被打倒在地,一时爬不起来。
就在这时,彭德怀突然大声喊道:「住手!我们早就分手了,她是无辜的!不要打她!」
那一刻,浦安修泪如泉涌。
这个男人,即使在最危难的时刻,想的还是保护她。而她,却在他最需要的时候离开了他。
批斗会后,浦安修的精神彻底崩溃了。
8月31日,她独自来到颐和园的昆明湖边。
望着波光粼粼的湖水,她掏出了准备好的安眠药。
「老彭,我来陪你了...」
她正要吞下药片,被晨练的群众发现,及时送医抢救,才捡回一条命。
醒来后,她望着医院的天花板发呆。
死不了,活着又有什么意义?那个她深爱的人,正在某个地方受苦,而她却无能为力。
岁月如流水,一晃就是七年。
1974年11月,初冬的北京格外寒冷。
这天,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突然来找浦安修。
看到侄女的表情,浦安修的心一沉。
「伯母」彭梅魁欲言又止。
「出什么事了?」
「伯伯他...他病得很重。」
浦安修霍地站起来:「在哪里?」
「在三〇一医院。医生说...说情况不太好。」
浦安修的手在发抖。这些年,她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彭德怀,想知道他的消息。现在终于有消息了,却是这样的噩耗。
彭梅魁小心翼翼地问:「嫂子,您...您要不要去看看伯伯?」
这个问题像一把刀,直刺浦安修的心。
去吗?她有什么脸面去见他?当年是她提出离婚,是她吃下了那半个梨。现在人家病危了,她却要去见最后一面,这算什么?
不去吗?这可能是此生最后的机会了。错过了,将是永远的遗憾。
浦安修在屋里踱来踱去,内心进行着激烈的斗争。
她想起彭德怀的音容笑貌,想起他们一起走过的峥嵘岁月。
从延安到太行山,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,多少个生死关头,他们都携手走过。
可是,她也想起那个秋天的下午,想起那个被摔碎的梨,想起彭德怀转身离去的背影。
「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他?」她喃喃自语。
彭梅魁等了很久,见浦安修始终没有回应,轻声说:「您再考虑考虑。伯伯他...可能撑不了多久了。」
11月29日下午2时52分。
浦安修正在家里看书,突然听到敲门声。打开门,是彭梅魁,眼睛红肿。
不用问,浦安修什么都明白了。
「什么时候?」她的声音异常平静。
「今天下午2点52分。」
浦安修扶着门框,才没有倒下去。
「他...他走的时候,有说什么吗?」
彭梅魁摇摇头,眼泪又流下来:「伯伯昏迷了好几天,一直没有醒过来。」
浦安修慢慢地走回屋里,坐在椅子上,呆呆地望着窗外。
窗外的天空灰蒙蒙的,就像她的心情。那个陪伴她二十四年的人,就这样走了。走得这样突然,这样无声无息。
而她,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。
「伯母,」彭梅魁小声问,「您要不要去...去送伯伯最后一程?」
浦安修沉默了许久,慢慢地摇了摇头。
她不配。一个在他最困难时离开的人,有什么资格去送他最后一程?
彭梅魁走后,浦安修关上门,拉上窗帘,在黑暗中坐了整整一夜。
她想哭,可是哭不出来。心里有个地方,空了。再也填不满了。
05
1976年,中国的天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10月,一个震动全国的消息传来。
虽然浦安修身在北师大,远离政治中心,但她敏锐地感觉到,风向变了。
街上的大字报少了,批斗会停了,人们脸上的表情也不再那么紧张。更重要的是,开始有人被平反了。
一个又一个熟悉的名字重新出现在报纸上,一个又一个「反党分子」恢复了名誉。浦安修的心里,燃起了一丝希望。
也许,彭德怀也能...
可转念一想,她又苦笑了。平反又如何?人都不在了,平反对一个死人来说,还有什么意义?
11月的一天,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来看她——杨献珍。
这位彭德怀的老朋友刚从外地「流放地」回到北京。多年不见,两人都老了许多。
「安修啊,」杨献珍开门见山,「老彭的事,可能要有说法了。」
浦安修的手颤了一下:「您是说...」
「中央在复查一些历史问题。老彭的案子,肯定会重新审查的。」
浦安修低下头,半晌没说话。
杨献珍也红了眼圈:「过去的事,就让它过去吧。」
「过不去!」浦安修摇头,「这辈子都过不去!您知道吗?他去世的时候,梅魁来问我要不要去见最后一面,我...我拒绝了。」
杨献珍愣住了。
「我没脸去见他。」浦安修哭着说,「我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了他,有什么资格去送他最后一程?」
「糊涂!真是糊涂!」杨献珍忍不住了,「他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,他走的时候你也不去,你让他多寒心啊!」
「我知道...我都知道...可是我...我真的没有勇气...」
两个老人相对而泣。
12月的一天,浦安修接到通知,要她去中组部一趟。
她心里一紧。这些年,每次接到这样的通知,都没有好事。
但这次似乎不一样,通知她的人语气很客气。
到了中组部,接待她的是一位年轻干部,满脸笑容:「浦安修同志,请坐。」
「同志」这个称呼,她已经很久没听到了。
「是这样的,」年轻干部说,「根据中央指示,我们正在复查一些历史遗留问题。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...」
听到「彭德怀同志」这几个字,浦安修的眼泪就下来了。多少年了,她再次听到有人这样称呼他。
「中央已经决定,要为彭德怀同志平反。」
平反!这两个字像惊雷一样在浦安修耳边炸响。
她等这一天,等了十七年。可真的等到了,她却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悲伤。
「浦安修同志,」年轻干部继续说,「作为彭德怀同志的夫人,我们想听听您的意见。」
夫人?浦安修愣了一下:「可是我...我当年提出过离婚申请...」
「那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事。」年轻干部说,「组织上理解。再说,你们并没有正式办理离婚手续,在法律上,你们还是夫妻。」
夫妻。这两个字让浦安修泪如雨下。
06
1976年12月24日,平安夜。
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,这只是个普通的日子。但对浦安修来说,这是她人生中最复杂的一天。
下午两点,两位中组部的工作人员来到她家。领头的是上次那位年轻干部,脸上带着喜悦的笑容。
「浦安修同志,我们带来了好消息!」
年轻干部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,郑重地递过来:「这是中央关于为彭德怀同志平反的决定。」
「彭德怀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军事家,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...」
「...在庐山会议上,彭德怀同志怀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诚之心,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,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,这是正常的...」
她放下文件,看着两位工作人员,终于问出了那个在心里盘桓了很久的问题:
「请问...他去世的时候,知道自己会被平反吗?」
这个问题来得太突然,两位工作人员对视了一眼,都沉默了。
过了许久,年轻干部才艰难地开口:「彭老总去世时...平反工作还没有开始...」
「就差两年,就差两年啊...」
07
1978年12月24日,人民大会堂。
时隔两年,又是12月24日。
「老彭,今天给你开追悼会了。」
彭梅魁来接她。车子缓缓驶向人民大会堂,浦安修望着窗外,思绪万千。
走进大会堂,她看到了彭德怀的遗像。
那是一张年轻时的照片,彭德怀穿着军装,目光炯炯。
。
致悼词的领导说:「彭德怀同志的一生,是革命的一生,战斗的一生,光辉的一生...」
每一句赞美,都像一把刀割在浦安修心上。是的,他是英雄,是功臣。可在他最需要理解的时候,连她这个最亲的人都离开了他。
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上的意见,是出于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关心...」
听到这里,浦安修再也忍不住,掩面而泣。
十九年前,就是因为这个「意见」,他们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。如果当时就能有这样的认识,该有多好。
追悼会进行到一半,工作人员端上来一个盖着红布的盒子。
「这是彭德怀同志的骨灰。」
浦安修颤抖着接过骨灰盒。
十六年了,这是她第一次这样「拥抱」他。
「老彭...」她哽咽着,说不出话来。
这时,工作人员又递过来一个小包:「这是彭老总的遗物。」
浦安修打开包,里面只有几件简单的东西:一支钢笔,一块旧手表,几张照片,还有一张折叠的纸条。
她展开纸条,上面是彭德怀的笔迹,只有八个字:
「相信历史是公正的。」
看到这八个字,浦安修泣不成声。
08
追悼会后,组织上考虑到浦安修的身体和生活,要给她安排更好的住房,提高待遇。
浦安修都拒绝了。
「我不配。」她说,「我在老彭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了他,现在他平反了,我凭什么享受这些?」
工作人员劝她:「您是彭老总的夫人,这是您应得的。」
「夫人?」浦安修苦笑,「我配吗?」
最终,她只接受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。其余的,一概不要。
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一件事上:整理彭德怀的著作。
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彭德怀的许多手稿在动乱中散失了,要一点点搜集。浦安修不顾年迈体弱,四处奔走。
「为什么要这么拼命?」有人问她。
「这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事了。」她回答。
1979年春天,她找到了彭德怀当年的秘书。
「浦老,您怎么来了?」秘书很惊讶。
「我想请您帮忙,整理老彭的自述。」
秘书眼圈红了:「彭老总的自述,有一部分手稿在我这里。但...但当年形势所迫,我不敢保存,烧了一些...」
「还有多少?」
「大概三分之一。」
「够了。」浦安修如获至宝,「有三分之一就够了。」
接下来的日子,浦安修几乎住在了秘书家里。她戴着老花镜,一字一句地辨认彭德怀的笔迹,一页一页地整理。
有时候,看到彭德怀写的一些话,她会突然停下来,老泪纵横。
比如这一段:「我这一生,对党、对人民是问心无愧的。唯一的遗憾,是没能看到祖国的完全统一...」
「老彭啊老彭,」她喃喃自语,「你对得起党,对得起人民,可我对不起你啊。」
1981年,在她的努力下,《彭德怀自述》终于整理完成。
出版社的编辑来取稿时,她郑重地说:「这本书的稿费,我一分钱都不要,全部捐给希望工程。」
「为什么?」
「老彭一生清廉,我不能用他的名义赚钱。」
《彭德怀自述》出版后,引起巨大反响。短短几年,发行了290万册。许多读者来信,说是通过这本书,才真正了解了彭德怀。
除了整理著作,她还为那些因彭德怀受牵连的人奔走。
在她的努力下,许多人得到了平反,恢复了名誉。
1985年,她的身体越来越差了。医生建议她住院,她拒绝了。
「我的时间不多了,还有很多事要做。」
1991年春天,她病重住院。
弥留之际,她握着彭梅魁的手说:「梅魁,我有个请求...」
「伯母,您说。」
「我死后...能不能...能不能把我葬在老彭旁边?」
1991年5月2日,浦安修去世,享年73岁。
按照她的遗愿,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,与彭德怀相邻。
三十二年的分离,终于在另一个世界重聚。
他等了一辈子的清白,她悔了一辈子的选择——历史最残酷的地方,是它从不给人改错的机会。
浦安修用她的一生,诠释了什么叫「悔恨」。
而彭德怀用他的一生,诠释了什么叫「信念」。
两个人,两种选择,一样的悲剧。
牛盘宝配资,哪个平台买股票好,盟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